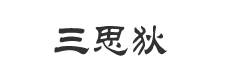董鸡其实是秧鸡的一种。
秧鸡不大,腿尤其细小,翅短圆,尾短,脚大,趾长。除高纬度地区外,遍布全球。我们这一片儿,形容一个人瘦到腿细,就形容她长一双“秧鸡脚杆”,又是野鸡。
董鸡是中型涉禽。雄鸟头顶有像鸡冠样的红色额甲,其后端突起游离呈尖形,全体灰黑色,下体较浅。雌鸟体较小,额甲不突起,上体灰褐色。
黄河
每到春天,秧苗在秧田里嫩绿的时候,田里就多了两种“野鸡”:秧鸡与董鸡。秧鸡,故名思义,就是在秧田里游走与生活的“野鸡”;董鸡则是根据它的叫声“咚”取名的。

那时节的春夜非常热闹,布谷鸟的叫声划过天空,秧鸡在田里“咕噜咕噜”地歌唱,董鸡则“咚咚咚”伴奏着;青蛙更是不甘寂寞,十里合唱连成一片;蟋蟀则此起彼落地弹琴重奏,整个田野仿佛赛歌会一般。
没有月亮的夜晚已经很美好了,有月亮的夜晚更是充满诗情画意。乡村的夜晚,自有一种野趣。

少年时我总想跟踪秧鸡与董鸡的行踪,但它们都是机灵鬼,当你离它远远的时候,它们唱得非常欢;当你离它们稍近时,它们就鸦雀无声了。我很是生气,捡起石块与泥块朝它们刚才鸣叫的地方打去,但它们依然毫无反应,弄得我只能泄气地离去。
但一待我离去,他们立即又欢快地歌唱起来,仿佛向我示威一般,于是我再无办法,只能早早卧在床上心痒难耐地听它们欢唱与跳跃。后来睡意渐渐袭来,我就到梦里与它们做迷藏去了。有时梦见抓住了一只乌黑的秧鸡,它却狠狠一嘴啄在我手上,让我赶紧撒手。醒来发现一只长脚蚊子叮在我手背上,我迷迷糊糊用另一只手掌拍过去,于是手背上溅起星星点点的血迹……
秧鸡和董鸡通常是在傍晚就开始歌唱了,而我有足够的耐心去跟踪它们。它们当然也并不畏惧我这样的野小子,只是在秧田里机警地与我嬉戏。通常,我从秧田这一头下去,它们从那一头钻出来。等我快步从田埂绕过去,它们又在另一片秧田出现了,气得我直跺脚。有时,它们会贼头贼脑从田埂某一段探出脑袋来,然后一溜烟又缩了回去。总之,我想捉到它们,注定是劳而无功的。

从春天到夏天,我们就做着这样的游戏,年复一年,直到我渐渐长大了,它们渐渐长老了。我没见到过它们死去,却见到一拨又一拨小秧鸡和小董鸡慢慢成长起来。
秧鸡和董鸡就像所有的野鸡一样,它们飞不太高也飞不太远,但他们奔跑的速度却非常惊人,一个成人想要追赶一只成年的秧鸡或董鸡是非常困难的——更何况,它们还能飞呢!
秧鸡和董鸡大约也是以秧田里的小鱼小虾为食吧,也会吃些青草、草籽什么的——但这只是我的猜测。他们似乎是水陆两栖的,我也看到他们在田埂或苕地里或麻地里活动,但终究还是在水田里居多。
秧鸡与董鸡也会随着稻子的成熟而肥壮起来,而且开始在稻田里做窝。秧鸡的窝大致还是很粗糙的,他们会把稻子趟倒,形成一个明显的“窝”状,然后在里面生蛋与孵雏。我们如果发现稻田凹下去一圈,大致可以判断那就是秧鸡或董鸡的窝,八成就可以收获秧鸡蛋了。当然,秧鸡与董鸡也没那么笨,它们往往在稻田里有多处窝,有些窝只是行宫,从来不会在那里下蛋的。所以很多小伙伴也会希望落空,乘兴而去,败兴而归。你看秧鸡与董鸡还是很狡猾的对吧?那当然了,不然它们又怎么能繁衍到现在呢?
我小时候是多次取到秧鸡或董鸡的蛋的,因此总有意外的口福。那秧鸡的蛋是麻叽叽的,就像鹌鹑蛋一样,当然比鹌鹑蛋大多了;那董鸡蛋则是一片色的,就像鸽子蛋一样。只是它们,大致都有初生蛋那么大小,煎炒出来则妙不可言。
后来,我们就要割稻谷了,秧鸡与董鸡也慢慢上了岸。但它们去了哪里,又在哪里过冬,我实在是不知道的。而年少的我的精力主要还是花在搜索秧鸡窝或小秧鸡上。那时还是大集体生产,那些拳头大小的小秧鸡,会随着被放倒的稻子,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奔逃。一旦发现了一窝小秧鸡,打谷子的人们会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计,以百米短跑的速度,四散追捕这些小秧鸡。不管它们怎样逃跑,八成还是逃不脱人的魔爪,然后成了他们下工后打牙祭的美味。我当然也参与过追捕小秧鸡的队伍,并成功捕捉到其中的几只。我那时还舍不得吃了它们,就用绳子拴住它们的脚,把他们养起来。但后来不知怎么的,他们总是消失了,或许成为了猫或黄鼠狼的美食了吧?现在想起来,可真是罪过啊!但那时,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和鸟类的概念,它们的命运,也大致就只能如此了。今天什么都开始要保护了,但我们却开始慢慢退化了——今天的我,肯定跑不过一只小秧鸡的。